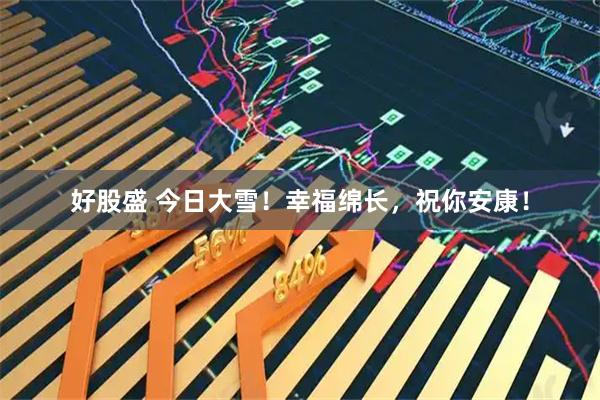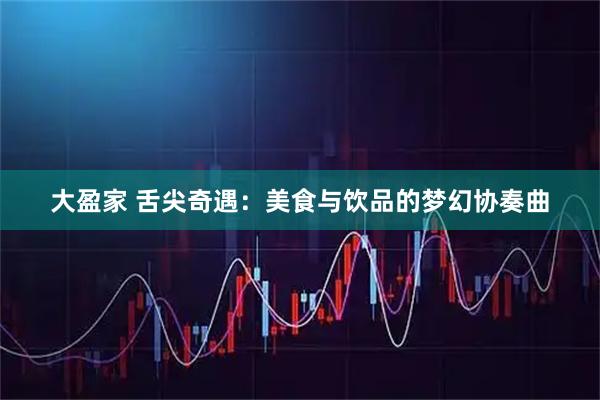“2009年8月10日中午博远配资,把我送到扶眉吧……”病房里,刘懋功声音微弱,却透着不容置疑。家属正忙着调点滴,猛地抬头,一时没有接话——这不是第一次听到老人提起扶眉,但从未听得如此急切。
很多人觉得,参加过那么多恶战,胸口别着一排勋章的刘懋功,理应和战友们一起躺进烈士陵园。可依照民政部《烈士褒扬条例》,烈士必须是因公牺牲,且有官方批复。刘懋功1955年授少将衔,历次负伤却都活了下来,他是一名参战老兵、功臣,却并不属于“烈士”范畴。规定就是规定,这让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的管理员犯了难。

把目光拉回1949年,那条严谨的法规还未成形,西北沙场的硝烟却已弥漫到人喘不过气。七届二中全会后,中央将第十八、第十九兵团划归彭德怀麾下,一野兵力激增。蒋介石急红了眼,令联合“二马”纠集二十多万兵力,意图在渭河北岸一锤定音。西安紧张得像一根满弦的弓,一触即发。
开战前,前委判断:“钳胡打马”,先拖住胡宗南,再收拾两马。可毛主席电令飞来:“钳马打胡”才是最优解。十师成了撞锤,挥手去敲胡宗南的主力。那会儿刘懋功刚调任师长,心里有数:这一次是硬骨头,啃不下来就要掉牙。
军以上会议气氛凝重,地图上的红蓝箭头交错。刘懋功想张嘴,被政委压低声线拦住:“别提。”副军长同样一句“不能提”。按说军令如山,可他琢磨地形、路程、月光,死死攥着那股较真劲儿,最终站起身:“司令员,我请示。”他在地图前划出一条蜿蜒线博远配资,提出提前出发、分三梯队轻装夜行。司令员皱眉:“敌人早逃呢?”刘懋功拍着图纸:“封锁道路,我担保一个都跑不掉。”最终计划敲定,他踩着夜色狂奔回师部。
当天下午,第一梯队离开驻地,摸到法门寺时发现敌军占寺。刘懋功让尖兵绕行,连翻四道沟,趟过几条细河,才抵益店。距离天亮不足四小时。俘来敌哨兵交出暗号,他索性带着部队直插敌营。等对方哨兵回过味,解放军已进二十米。手榴弹一阵爆响,敌阵瞬间乱成麻。刘懋功穷追不舍,顺势拿下罗局镇与眉县火车站,切断胡宗南西逃咽喉。

紧接着的遭遇战更凶险:敌六十五军前卫团摸黑扑来,火力猛,队形整。刘懋功命炮兵阵地就地展开,后续梯队箭头般插进敌群。不到一小时,对方被撕成数段,全歼。交换伤亡数字时,参谋长沉默地低下头——我军也付出不小代价。
进入盛夏,西北黄土地曝晒,部队连续急行军十四小时,又顶住敌军反扑十二小时。有人在行军途中热倒再也没醒;有人为给战士送水被流弹击中;剩下的人嚼着苞谷秆坚持射击。多日高温,刘懋功两眼充血,眼皮肿得像桃子,军医拿生理盐水一盆接一盆往他眼里倒,他就坐在路边指挥作战,连眉头都没皱。
罗局守住了,胡宗南主力溃散,扶眉战役胜负至此逆转。一野在西北站稳脚跟博远配资,随后三大战役的尾声呼啸而来。十师官兵牺牲近两千,名册厚得像一砖头。刘懋功清点完烈士名单,久久没合眼,他跟身边的警卫员说:“这些名字要刻在石头上,让后人记得。”警卫员点头,悄悄抹泪。

到了2003年清明,新落成的扶眉战役纪念馆邀请刘懋功揭幕。老将军在展柜前缓慢踱步,望着熟悉的缴获炮、缴获旗,眼中浮起水汽。他站到窗边,看见不远处的新陵园,嘀咕一句:“要是将来能躺那里,就圆满了。”工作人员没敢接口,只在旁陪着。
2009年,他再度提及这一愿望。家属奔走数日,陵园管理员有心帮忙,却给出一句实话:“您不能算烈士。”随后建议求兰州军区特批。消息传回病房,刘懋功摆手:“党规军纪不能抹平。活着服从,走了照样服从。”这一句话,说得淡,却像一枚准星。
最终,他遵照规定葬于家乡公墓。一块深灰色花岗岩碑,碑文没有华丽辞藻,只写“原十师师长刘懋功同志长眠于此”。军礼响起时,几位参过扶眉的老兵抬头敬礼,脸上泪沟纵横。一位连级干部轻声念叨:“师长还是那个师长,一点没变。”
多少年后,人们在纪念馆里看见刘懋功留下的作战手令,依旧能嗅到火药味。我时常想,若没有那次夜行军、那些趟河翻沟的身影,西北战场局势会否拖上数月?当然,历史没有如果,它只认成败,也只认规矩。刘懋功生前一向刚直,去世时依旧让规矩落地——这或许比躺进烈士陵园更能说明他的品格。

有人评论:“条例太死板。”我倒觉得,这恰恰凸显制度的公信力。把功臣与烈士区分开,是为了让“烈士”二字永远沉甸甸。刘懋功懂,管理员懂,部队更懂。正因如此,他没强求,也没人徇私。规矩立住了,英雄的分量反而更重。
日后再去扶眉战役纪念馆,抬眼就能见到墙上一行小字——“十师全体指战员,5000余烈士长眠于此”。刘懋功不在陵园,却与这段文字并肩。他的骨灰埋在故土,名字刻在史册,战友的名字刻在石碑。各归其位,恰好。
熊猫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